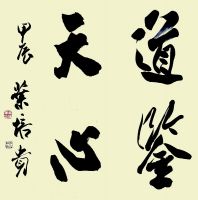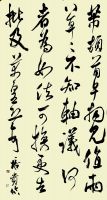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4年06月04日期 第04版:人物专访
中国书法需要重续文脉重回生活
——访北京书协主席叶培贵
■本报记者 梅雁
北京作为书法重镇,名家云集,新人辈出。首都书法家如何熔铸古今、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北京书法家协会如何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北京书协主席叶培贵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这些话题作了深入的解答。
从艺之路:
谨遵中石先生严令“学古人而不能学老师”
问: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欢书法,高中时还获得过福建省中小学生美术书法比赛一等奖,大学上的却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上很多大书法家比如二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人的书法创作都是文人书法。您当时是否就立志走文人书法之路?中文系的学习对您此后从事书法艺术有什么帮助?
答:这个问题需要分层回答。先说第一层。我高中时哪里知道“文人书法”啊?!报考北师大中文系而没有直接报考书法专业,主要原因是普通高考和艺术高考是分开的,我高中阶段在文科班(那时候高中分文理科),准备参加的始终就是普通高考。再说第二层。狭义的“文人书法”是个复杂的概念,不能说古代知识人就都是“文人”,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二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人的书法”都称作“文人书法”。放到当代,更不能说读了中文系就是“文人”了。因此,即便我能写写诗、作作文,也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文人”,我的书法就是“文人书法”。还有第三层。中文系的知识体系,确实对我从事书法教学、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书法离不开文字和诗文及其背后所关联的历史文化。启功先生很强调“文史常识”,欧阳中石先生认为“文史常识”其实是字内功而不是字外功。很幸运,北师大中文系为我打下了一些基础,使我略明字理,稍知文史。但因为驽钝,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老先生们的要求。
问:您在首都师范大学师从欧阳中石先生,获得文学(书法)博士学位。请问中石先生对您的书法创作有哪些影响?
答:欧阳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为人、为学、为艺,无所不在。仅就书法创作而言,最核心的是入学之初怹就严令的“学古人而不能学老师”,我是奉行至今——从来没有临写过怹的字,哪怕是一个笔画。因为这个要求,我就必须努力师法古人并尝试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惭愧的是,我拜入门墙后,有12年时间侍奉怹,包括裁纸和按纸,耳濡目染太直接太丰富,我有很多书写习惯仍然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我理解古法提供了很大帮助,但也确实使我违背了怹老人家的要求。这是我才能不足导致的结果,愧对老师。但怹的要求,我始终铭记,也一直在继续努力践行。
问:您曾经向哪些古代书法家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到什么营养?
答:我们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要求至少临过50种帖,相当于外语学习的“泛读”,所以不敢说是“学习”,只算有所了解。真正用功较多的,有米芾、王羲之、李邕和褚遂良。我处理笔法的许多办法来自米芾和褚遂良,结构受到李邕的启发,气息上又希望能对王羲之有所领略。但仍然是因为驽钝的原因,都还很皮毛。
问:您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书法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答:“优秀”不好界定,古代书家的“优秀”样本也是多种多样,很难简单概括。但苏轼曾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知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这三方面应该是较为重要的。“识”对应“心”,“见”对应“目”,“学”对应“手”。“目”“手”相对好理解,视野过窄、训练不足,显然都是制约。“心”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鉴别力、判断力、感悟力等较为本体的东西,但仅有这些可能还不够,还要有对天、对人、对史、对时以至于对民族文化核心精神、核心价值等等的认知和体验。
问:回望数十年书法艺术生涯,您最想对年轻一代书法学子们提的建议是什么?
答:时间的长短不代表行走的远近,我自己还在路上,所以不好说是建议,顶多算是共勉吧。第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真的爱好甚至是以之为乐,才可能持久地做下去,因为做的过程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第二,不要拘泥于单一目标,书法是一个大的文化生态,不一定只有“创作”才是做书法,理论研究、展览策划、收藏传播、教育普及等等,也都是书法这一文化生态圈的重要事情,能够发挥作用,就是好的书法工作者;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做哪一个领域的事情,都扎扎实实,耐得住、行得稳,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第四,艺术有个人性,但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要有家国情怀、文化责任、社会担当,才能使自己的艺术生涯与时代同频共振。
存在问题:
历史造成的“传承断裂”和“社会疏离”尚未充分解决
问:您如何看待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化方面的作用?
答:前面说过,书法离不开字、文,因此,通过书法,我们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中国字、中国文,进而切入更加深广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乃至参与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创造伟业。反过来说,书法可以使字、文进一步焕发艺术和文化的光彩,即使是信息化时代,电子产品里的字、文,也需要艺术和文化来点亮。因此,书法在当代社会中,不仅没有因为信息化而渐趋消亡,事实上反而是古代优秀书法遗产借着信息化的手段而活化,甚至是进一步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我们可以循此而入,通过书法教育、社会传播以及学术研究、艺术创造,使凝聚在其中的民族的“精气神”不仅充分展现,而且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书法是中国原生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是最为独特的艺术之一,对于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践行第二个结合,更好地掘进“历史纵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建设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进一步开拓“创新空间”,创造中华新文化,都可以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问:您认为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对当代文化建设有何影响?
答:我对这个问题在宏观上的看法与前一个问题相似,只有从孩子抓起,上述宏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但在微观上还可以略作补充。汉字学习离开了“写”,很难真正扎实真正深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书法学习对于学习者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因此实际上具有三层次的意义:一是辅助语文学习;二是促进身心健康;三是用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高素质人才(包括未来的书法人才)的培养。
问:您多次担任重要艺术和文化奖项评委,请问您认为当下中国书法现状存在什么问题?
答: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传承断裂”和“社会疏离”尚未充分解决。具体来说,一方面,书法本身在1905年开始采用新学制后长期被边缘化,既没有接受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洗礼,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格局也未能持续,而是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书法所依托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土壤,在近百年来也发生了剧烈变化,长期边缘化的书法未能与之同频共振,也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逐渐窄化为展厅或小圈子内的笔墨游戏。常常被社会诟病的书法创作中的误文、错字、违背书仪等问题,以及在继承与创新方面的种种缺憾,根本上说,都是上述历史问题造成的后果。幸运的是,启功先生、沙孟海先生、陆维钊先生、徐无闻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在他们的晚年,通过高等书法教育,延续了薪火。
问:您长期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出版了多部书法专著,您认为书法教育机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答:前述老先生们揭开了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大幕,奠定了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坚实根基,但遗憾的是时间不够长、范围不够广、建制不够宽,未及充分解决“断裂”和“疏离”问题。2022年,新版《学科目录》终于将书法列为“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一部分,且将“美术与书法”共同列为专业博士培养类别,书法在学科建制上获得了与其他艺术门类同等的发展空间。此外,2022年的《语文课标》也纳入了2014年《中小学书法教学指导纲要》的核心要求,使得书法教育完整、系统地进入我国教育体制。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宏图在书法领域的呈现。对于书法教育工作者来说,现在最为重要而且迫切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和努力,拿出既能够充分传承传统精神,又能够有效满足时代需要,足以支撑这一全新教育格局的成果来,使当代书法教育不仅在“硬”的机制层面上是完善的,而且在“软”的人才培养体系上也是完善的。 (下转5版)
北京作为书法重镇,名家云集,新人辈出。首都书法家如何熔铸古今、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北京书法家协会如何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北京书协主席叶培贵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这些话题作了深入的解答。
从艺之路:
谨遵中石先生严令“学古人而不能学老师”
问: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欢书法,高中时还获得过福建省中小学生美术书法比赛一等奖,大学上的却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上很多大书法家比如二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人的书法创作都是文人书法。您当时是否就立志走文人书法之路?中文系的学习对您此后从事书法艺术有什么帮助?
答:这个问题需要分层回答。先说第一层。我高中时哪里知道“文人书法”啊?!报考北师大中文系而没有直接报考书法专业,主要原因是普通高考和艺术高考是分开的,我高中阶段在文科班(那时候高中分文理科),准备参加的始终就是普通高考。再说第二层。狭义的“文人书法”是个复杂的概念,不能说古代知识人就都是“文人”,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二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苏轼等人的书法”都称作“文人书法”。放到当代,更不能说读了中文系就是“文人”了。因此,即便我能写写诗、作作文,也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文人”,我的书法就是“文人书法”。还有第三层。中文系的知识体系,确实对我从事书法教学、研究和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书法离不开文字和诗文及其背后所关联的历史文化。启功先生很强调“文史常识”,欧阳中石先生认为“文史常识”其实是字内功而不是字外功。很幸运,北师大中文系为我打下了一些基础,使我略明字理,稍知文史。但因为驽钝,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老先生们的要求。
问:您在首都师范大学师从欧阳中石先生,获得文学(书法)博士学位。请问中石先生对您的书法创作有哪些影响?
答:欧阳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为人、为学、为艺,无所不在。仅就书法创作而言,最核心的是入学之初怹就严令的“学古人而不能学老师”,我是奉行至今——从来没有临写过怹的字,哪怕是一个笔画。因为这个要求,我就必须努力师法古人并尝试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惭愧的是,我拜入门墙后,有12年时间侍奉怹,包括裁纸和按纸,耳濡目染太直接太丰富,我有很多书写习惯仍然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些影响对我理解古法提供了很大帮助,但也确实使我违背了怹老人家的要求。这是我才能不足导致的结果,愧对老师。但怹的要求,我始终铭记,也一直在继续努力践行。
问:您曾经向哪些古代书法家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到什么营养?
答:我们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要求至少临过50种帖,相当于外语学习的“泛读”,所以不敢说是“学习”,只算有所了解。真正用功较多的,有米芾、王羲之、李邕和褚遂良。我处理笔法的许多办法来自米芾和褚遂良,结构受到李邕的启发,气息上又希望能对王羲之有所领略。但仍然是因为驽钝的原因,都还很皮毛。
问:您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书法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答:“优秀”不好界定,古代书家的“优秀”样本也是多种多样,很难简单概括。但苏轼曾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知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这三方面应该是较为重要的。“识”对应“心”,“见”对应“目”,“学”对应“手”。“目”“手”相对好理解,视野过窄、训练不足,显然都是制约。“心”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鉴别力、判断力、感悟力等较为本体的东西,但仅有这些可能还不够,还要有对天、对人、对史、对时以至于对民族文化核心精神、核心价值等等的认知和体验。
问:回望数十年书法艺术生涯,您最想对年轻一代书法学子们提的建议是什么?
答:时间的长短不代表行走的远近,我自己还在路上,所以不好说是建议,顶多算是共勉吧。第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真的爱好甚至是以之为乐,才可能持久地做下去,因为做的过程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第二,不要拘泥于单一目标,书法是一个大的文化生态,不一定只有“创作”才是做书法,理论研究、展览策划、收藏传播、教育普及等等,也都是书法这一文化生态圈的重要事情,能够发挥作用,就是好的书法工作者;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做哪一个领域的事情,都扎扎实实,耐得住、行得稳,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第四,艺术有个人性,但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要有家国情怀、文化责任、社会担当,才能使自己的艺术生涯与时代同频共振。
存在问题:
历史造成的“传承断裂”和“社会疏离”尚未充分解决
问:您如何看待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化方面的作用?
答:前面说过,书法离不开字、文,因此,通过书法,我们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中国字、中国文,进而切入更加深广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乃至参与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创造伟业。反过来说,书法可以使字、文进一步焕发艺术和文化的光彩,即使是信息化时代,电子产品里的字、文,也需要艺术和文化来点亮。因此,书法在当代社会中,不仅没有因为信息化而渐趋消亡,事实上反而是古代优秀书法遗产借着信息化的手段而活化,甚至是进一步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我们可以循此而入,通过书法教育、社会传播以及学术研究、艺术创造,使凝聚在其中的民族的“精气神”不仅充分展现,而且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书法是中国原生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是最为独特的艺术之一,对于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践行第二个结合,更好地掘进“历史纵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建设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进一步开拓“创新空间”,创造中华新文化,都可以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问:您认为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对当代文化建设有何影响?
答:我对这个问题在宏观上的看法与前一个问题相似,只有从孩子抓起,上述宏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但在微观上还可以略作补充。汉字学习离开了“写”,很难真正扎实真正深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书法学习对于学习者个体的身心健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因此实际上具有三层次的意义:一是辅助语文学习;二是促进身心健康;三是用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高素质人才(包括未来的书法人才)的培养。
问:您多次担任重要艺术和文化奖项评委,请问您认为当下中国书法现状存在什么问题?
答: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传承断裂”和“社会疏离”尚未充分解决。具体来说,一方面,书法本身在1905年开始采用新学制后长期被边缘化,既没有接受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洗礼,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格局也未能持续,而是出现了断裂;另一方面,书法所依托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土壤,在近百年来也发生了剧烈变化,长期边缘化的书法未能与之同频共振,也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逐渐窄化为展厅或小圈子内的笔墨游戏。常常被社会诟病的书法创作中的误文、错字、违背书仪等问题,以及在继承与创新方面的种种缺憾,根本上说,都是上述历史问题造成的后果。幸运的是,启功先生、沙孟海先生、陆维钊先生、徐无闻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在他们的晚年,通过高等书法教育,延续了薪火。
问:您长期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出版了多部书法专著,您认为书法教育机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答:前述老先生们揭开了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大幕,奠定了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坚实根基,但遗憾的是时间不够长、范围不够广、建制不够宽,未及充分解决“断裂”和“疏离”问题。2022年,新版《学科目录》终于将书法列为“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一部分,且将“美术与书法”共同列为专业博士培养类别,书法在学科建制上获得了与其他艺术门类同等的发展空间。此外,2022年的《语文课标》也纳入了2014年《中小学书法教学指导纲要》的核心要求,使得书法教育完整、系统地进入我国教育体制。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宏图在书法领域的呈现。对于书法教育工作者来说,现在最为重要而且迫切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和努力,拿出既能够充分传承传统精神,又能够有效满足时代需要,足以支撑这一全新教育格局的成果来,使当代书法教育不仅在“硬”的机制层面上是完善的,而且在“软”的人才培养体系上也是完善的。 (下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