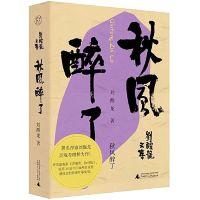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3年12月26日期 第05版:副刊·电影
作家刘醒龙和导演黄建新对谈
说透了这个时代电影的风险与机遇
■张潇潇
在最近举办的北影大讲堂顶峰对谈上,作家刘醒龙犹豫了许久,终于还是对着黄建新导演,说出了那个让他耿耿于怀了多年的心结。原来是一部1994年上映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改编自他1992年首发在《长江文艺》的中篇小说《秋风醉了》。作为黄建新导演的城市三部曲的终篇,不仅在当年收获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并且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5分,被年轻影迷们尊为“描写体制内生活的神作”。而刘醒龙发现片中原本淳朴的父亲被改成心机深重的恶毒角色,他认为虽然只是一个人物细微的改变,文学精神变了。黄建新则笑着回答,幸好你没看过剧本咱俩就合作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低廉的版权费,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和改编限制,作家和导演对彼此专业这样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这是文学界和电影界的普遍现象。黄建新拍摄的《黑炮事件》《轮回》《埋伏》《五魁》《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打左灯向右转》,分别改编自张贤亮、王朔、方芳、贾平凹、邓刚、刘醒龙和叶广芩7位作家的小说。他感到很幸运的是,这7位著名作家都对电影改编内容没有干涉过一分一毫。
那是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紧密结合的时期,也正因为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滋养,第五代导演不约而同地在1994年前后达到创作巅峰。那一年,张艺谋拍出《活着》,陈凯歌拍出《霸王别姬》,田壮壮拍出《蓝风筝》,黄建新拍出《背靠背,脸对脸》。
黄建新回溯了中国电影史上比较好的电影,包括《活着》,其实都是小说改的。畅销的《哈利波特》,也是小说改的。黄建新对电影文学性的回归表示乐观,他说前不久上映的、由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就是改编自余华小说,作为文艺片都卖了3个多亿,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提起电影改编小说,黄建新认为,小说在人物、在深度特别在心理联想上都是超过电影的,因为电影只有一个具象,所有人都得顺着你说的景,先消除了自己的空间联想来跟着你,这也成为电影改编小说的难点。因为100个人有100个联想,对着你的联想,你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就变得特别重要,所以电影的二度创作,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把它真正转化成电影,具备电影的魅力。
具体在做《背靠背,脸对脸》的改编时,为这个现实主义故事寻找审美距离,成了黄建新最大的挑战。故事发生在文化馆,而一般地方的文化馆,大部分都是在比较现代化的办公楼里,这让他觉得故事缺乏视听上的奇观。“我觉得找不着电影语言。小说写得那么好,我如果那么拍,肯定出来特别糟糕。”
直到一次,他看到西影厂的《猴年耍猴》。耍猴人晚上住在山上的庙里。“我看到他的景就愣了,电影语言被激活了。第二天,我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就去了河南,勘完景觉得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因为这个山上会馆是一个关帝庙,这个庙宇里形成了语汇,变成了既亲近真实又疏离缥缈的一个东西。”
电影中,庙堂般的文化馆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象征,腐朽守旧,但又沉重恢宏,让年轻人在其中的博弈如同螳臂当车。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像这座迷雾中的庙宇,表面上背靠背脸对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作掩盖了背后的勾心斗角,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中,家庭和职场激烈的权力争夺又被温情脉脉的人情模糊软化。
通过关帝庙,黄建新成功地在现实主义故事中找到了电影的美学体系,又以庙宇为核心,特别设计了外部的景,为了保持表演的真实感,即使拍下雪两个人的戏,导演也派了上百个人去维持周围,用精心的编排营造抓拍的感觉,来维持电影的文学气息,同时又加强了原著故事中的戏剧性。
刘醒龙直言,作为原著作者,建议年轻作家版权卖了就可以了,电影怎么拍不要管,“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要自己改自己的作品。因为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谈起自己的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时,跟剧组并不愉快,因为爱较真,对电影的很多改动无法接受。后来才明白,电影有电影的规律,文字展现它有它自身的魅力,有些情节,小说里面是正面说的,电影则需要反面说。
谈到现实主义创作。刘醒龙表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主流,就像长江的主河道是生命的源泉,年轻时很容易被支流的技巧和花活吸引,年纪渐长才重新发现现实主义写作的价值。他说,永远不要低估了读者,不要以为读者水平低,刻意迎合读者。类比到电影,他谈到相比精美的好莱坞电影,他反倒喜欢看那些尽管拍得不是很好,却令人心动的电影。
黄建新认为,转向市场化的主流电影则更是行业危机驱动的。上世纪90年代,在各大国营制片厂大力支持艺术探索之时,电影市场却极其惨淡,票房低迷。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和中美关系的变化,1994年,电影局提出1995年开始,每年可以采用分账形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次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真实的谎言》在国内上映,好莱坞大片的大场面快节奏和特效给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远高于于国产电影的票价却引得人们排队买票,最终该片成为首部过亿票房的海外电影。
彼时,黄建新及与他同时期的第五代导演还在各大电影节学习着标新立异的新风格。国产电影低迷的现状和好莱坞大片的热映却让他意识到,中国老百姓要看的电影,普通观众要看的电影,市场上却没有。
黄建新认为,中国电影得有人出来推动产业发展,“中国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主流市场,中国电影就没了。”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主流市场,才会有人投艺术电影,它是相辅相成的。
从那以后,他开始转向市场电影的创作,并为多部商业电影担任制片和监制,希望把华语电影的主流市场做出来,来支撑电影工业,来支撑我们原来的理想。“我当时立志,用10年时间让中国电影跟欧美和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占到60%票房。现在,尽管有好莱坞电影上映,我们的票房也能稳定地占到70%,这样中国电影还在。如果国产电影只有20%的票房,国产电影就没了。就像美国电影在很多国家把本土电影业淹没了,如果我们不努力,国产电影市场也许早就没了。”
尽管如今好莱坞大片不再有主导中国市场的威胁,但黄建新坦言,电影行业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高强度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的注意力和娱乐方式都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AI、VR等新的科技也极大地颠覆着整个电影行业。如今电影行业一年的总票房在500亿左右,由于时间成本和观众娱乐方式的碎片化,电影院观众每年都在流失。
与此同时,来势汹汹的短视频、竖屏短剧却以一天一亿的收入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一些霸道总裁故事被好莱坞购买了版权。黄建新看过这些短剧后,觉得它有点像改革开放时地摊文学中写得最好的那部分,“它特别直接,直接到让你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你只能跟着它走。”并且培养了一批演员,形成了一种美学体系。黄建新在思考,如果碎片化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必然,那么电影的优势在哪里?创作者又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如果说观众流失是电影在市场端面临的挑战,AI则直接从电影的生产环节颠覆了整个行业。今年,好莱坞编剧演员的罢工,已经传达出编剧和演员作为内容生产者的AI焦虑。黄建新作为具有产业高度和国际视野的导演和制片,也表达了电影人的AI焦虑。
比如AI技术宣告了原有CGI技术的死亡,特效行业里很多公司重金修建的虚拟棚,还没投入使用就被淘汰。郭帆导演告诉他,美国两个华人女孩创造出了直接生成视频内容的AI,“我刚才在开玩笑,导演没用了,我给你讲故事出来视觉。你说这个视觉不是我想的,他就给你改。10天时间每天讲一段,它就变成一部完整的视觉电影。”在AI生成的电影里,不仅导演没有出现的必要,连整个摄制组都不复存在。
无论焦虑还是恐惧,AI都势不可挡、必将到来。黄建新一直希望自己不要因为岁数大了而抵御新的科技,而是积极思索新的创作方式。
“人类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电影在这样一个崭新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面临的新内容。就是当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于黄建新的焦虑,刘醒龙对于AI显得更加乐观,他始终相信人的写作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这是写作者必须有的强大自信,否则不用AI,周围人的质疑就可以让人停笔。他认为,文学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来源于生活,是人扎根在生活最深处所获得的体悟。你一开始不了解,突然你发现了,写出来了,其他人才知道。
黄建新和刘醒龙都建议年轻创作者多体验生活,多读书,多出门,多结交不同阶层的朋友。艺术源于生活,生活的细节远比想象的高明。
不过,黄建新也表示,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困难,而年轻人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听建议,而且年轻人对生活的体验更敏感。黄建新表示,目前除了做主流电影,他还会投资一些小体量的电影。去年黄建新投资了张律导演在北影节获奖的《白塔之光》。在金鸡创投上发掘了青年导演廖飞宇自编自导的《屋顶足球》。当时电影拍了70%没钱了。黄建新给他追加了两三百万让他去补拍,在戛纳市场反映不错。
黄建新认为,市场是双向的,只要有才华,市场会给出回报。同时他也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所有的大导演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奠定的基础,而且回过头来大家会说第一部戏、第二部、第三部是最好的戏,因为他是没有私心地去展示他的灵魂。
“年轻人要利用最单纯的创意去努力,要学会接触人,如果拿到了一个好的故事和设想,如果讲述得好或者拍的短片好,我认为是找得到投资的。”
(摘编自北影大讲堂公众号)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低廉的版权费,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和改编限制,作家和导演对彼此专业这样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这是文学界和电影界的普遍现象。黄建新拍摄的《黑炮事件》《轮回》《埋伏》《五魁》《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打左灯向右转》,分别改编自张贤亮、王朔、方芳、贾平凹、邓刚、刘醒龙和叶广芩7位作家的小说。他感到很幸运的是,这7位著名作家都对电影改编内容没有干涉过一分一毫。
那是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紧密结合的时期,也正因为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的滋养,第五代导演不约而同地在1994年前后达到创作巅峰。那一年,张艺谋拍出《活着》,陈凯歌拍出《霸王别姬》,田壮壮拍出《蓝风筝》,黄建新拍出《背靠背,脸对脸》。
黄建新回溯了中国电影史上比较好的电影,包括《活着》,其实都是小说改的。畅销的《哈利波特》,也是小说改的。黄建新对电影文学性的回归表示乐观,他说前不久上映的、由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就是改编自余华小说,作为文艺片都卖了3个多亿,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提起电影改编小说,黄建新认为,小说在人物、在深度特别在心理联想上都是超过电影的,因为电影只有一个具象,所有人都得顺着你说的景,先消除了自己的空间联想来跟着你,这也成为电影改编小说的难点。因为100个人有100个联想,对着你的联想,你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就变得特别重要,所以电影的二度创作,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把它真正转化成电影,具备电影的魅力。
具体在做《背靠背,脸对脸》的改编时,为这个现实主义故事寻找审美距离,成了黄建新最大的挑战。故事发生在文化馆,而一般地方的文化馆,大部分都是在比较现代化的办公楼里,这让他觉得故事缺乏视听上的奇观。“我觉得找不着电影语言。小说写得那么好,我如果那么拍,肯定出来特别糟糕。”
直到一次,他看到西影厂的《猴年耍猴》。耍猴人晚上住在山上的庙里。“我看到他的景就愣了,电影语言被激活了。第二天,我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就去了河南,勘完景觉得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因为这个山上会馆是一个关帝庙,这个庙宇里形成了语汇,变成了既亲近真实又疏离缥缈的一个东西。”
电影中,庙堂般的文化馆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象征,腐朽守旧,但又沉重恢宏,让年轻人在其中的博弈如同螳臂当车。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像这座迷雾中的庙宇,表面上背靠背脸对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作掩盖了背后的勾心斗角,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中,家庭和职场激烈的权力争夺又被温情脉脉的人情模糊软化。
通过关帝庙,黄建新成功地在现实主义故事中找到了电影的美学体系,又以庙宇为核心,特别设计了外部的景,为了保持表演的真实感,即使拍下雪两个人的戏,导演也派了上百个人去维持周围,用精心的编排营造抓拍的感觉,来维持电影的文学气息,同时又加强了原著故事中的戏剧性。
刘醒龙直言,作为原著作者,建议年轻作家版权卖了就可以了,电影怎么拍不要管,“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要自己改自己的作品。因为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谈起自己的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时,跟剧组并不愉快,因为爱较真,对电影的很多改动无法接受。后来才明白,电影有电影的规律,文字展现它有它自身的魅力,有些情节,小说里面是正面说的,电影则需要反面说。
谈到现实主义创作。刘醒龙表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主流,就像长江的主河道是生命的源泉,年轻时很容易被支流的技巧和花活吸引,年纪渐长才重新发现现实主义写作的价值。他说,永远不要低估了读者,不要以为读者水平低,刻意迎合读者。类比到电影,他谈到相比精美的好莱坞电影,他反倒喜欢看那些尽管拍得不是很好,却令人心动的电影。
黄建新认为,转向市场化的主流电影则更是行业危机驱动的。上世纪90年代,在各大国营制片厂大力支持艺术探索之时,电影市场却极其惨淡,票房低迷。随着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和中美关系的变化,1994年,电影局提出1995年开始,每年可以采用分账形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次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真实的谎言》在国内上映,好莱坞大片的大场面快节奏和特效给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远高于于国产电影的票价却引得人们排队买票,最终该片成为首部过亿票房的海外电影。
彼时,黄建新及与他同时期的第五代导演还在各大电影节学习着标新立异的新风格。国产电影低迷的现状和好莱坞大片的热映却让他意识到,中国老百姓要看的电影,普通观众要看的电影,市场上却没有。
黄建新认为,中国电影得有人出来推动产业发展,“中国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主流市场,中国电影就没了。”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主流市场,才会有人投艺术电影,它是相辅相成的。
从那以后,他开始转向市场电影的创作,并为多部商业电影担任制片和监制,希望把华语电影的主流市场做出来,来支撑电影工业,来支撑我们原来的理想。“我当时立志,用10年时间让中国电影跟欧美和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占到60%票房。现在,尽管有好莱坞电影上映,我们的票房也能稳定地占到70%,这样中国电影还在。如果国产电影只有20%的票房,国产电影就没了。就像美国电影在很多国家把本土电影业淹没了,如果我们不努力,国产电影市场也许早就没了。”
尽管如今好莱坞大片不再有主导中国市场的威胁,但黄建新坦言,电影行业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方面,高强度和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的注意力和娱乐方式都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AI、VR等新的科技也极大地颠覆着整个电影行业。如今电影行业一年的总票房在500亿左右,由于时间成本和观众娱乐方式的碎片化,电影院观众每年都在流失。
与此同时,来势汹汹的短视频、竖屏短剧却以一天一亿的收入吸引着观众的注意,一些霸道总裁故事被好莱坞购买了版权。黄建新看过这些短剧后,觉得它有点像改革开放时地摊文学中写得最好的那部分,“它特别直接,直接到让你都没有回旋的余地,你只能跟着它走。”并且培养了一批演员,形成了一种美学体系。黄建新在思考,如果碎片化成为了人类发展的必然,那么电影的优势在哪里?创作者又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如果说观众流失是电影在市场端面临的挑战,AI则直接从电影的生产环节颠覆了整个行业。今年,好莱坞编剧演员的罢工,已经传达出编剧和演员作为内容生产者的AI焦虑。黄建新作为具有产业高度和国际视野的导演和制片,也表达了电影人的AI焦虑。
比如AI技术宣告了原有CGI技术的死亡,特效行业里很多公司重金修建的虚拟棚,还没投入使用就被淘汰。郭帆导演告诉他,美国两个华人女孩创造出了直接生成视频内容的AI,“我刚才在开玩笑,导演没用了,我给你讲故事出来视觉。你说这个视觉不是我想的,他就给你改。10天时间每天讲一段,它就变成一部完整的视觉电影。”在AI生成的电影里,不仅导演没有出现的必要,连整个摄制组都不复存在。
无论焦虑还是恐惧,AI都势不可挡、必将到来。黄建新一直希望自己不要因为岁数大了而抵御新的科技,而是积极思索新的创作方式。
“人类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电影在这样一个崭新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面临的新内容。就是当下的现实主义。”
相比于黄建新的焦虑,刘醒龙对于AI显得更加乐观,他始终相信人的写作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这是写作者必须有的强大自信,否则不用AI,周围人的质疑就可以让人停笔。他认为,文学上最重要的部分,一定是来源于生活,是人扎根在生活最深处所获得的体悟。你一开始不了解,突然你发现了,写出来了,其他人才知道。
黄建新和刘醒龙都建议年轻创作者多体验生活,多读书,多出门,多结交不同阶层的朋友。艺术源于生活,生活的细节远比想象的高明。
不过,黄建新也表示,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困难,而年轻人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听建议,而且年轻人对生活的体验更敏感。黄建新表示,目前除了做主流电影,他还会投资一些小体量的电影。去年黄建新投资了张律导演在北影节获奖的《白塔之光》。在金鸡创投上发掘了青年导演廖飞宇自编自导的《屋顶足球》。当时电影拍了70%没钱了。黄建新给他追加了两三百万让他去补拍,在戛纳市场反映不错。
黄建新认为,市场是双向的,只要有才华,市场会给出回报。同时他也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业,所有的大导演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奠定的基础,而且回过头来大家会说第一部戏、第二部、第三部是最好的戏,因为他是没有私心地去展示他的灵魂。
“年轻人要利用最单纯的创意去努力,要学会接触人,如果拿到了一个好的故事和设想,如果讲述得好或者拍的短片好,我认为是找得到投资的。”
(摘编自北影大讲堂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