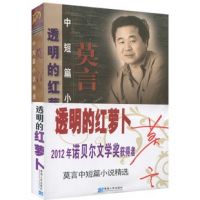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1年12月06日期 第05版:副刊·文学理论
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上接4版)
从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学就有一个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都被激进的反传统思潮所支配,处于进入现代剧烈变革中的中国,同时面临反帝反封建的重任,革命必须彻底,革命是解放和涅槃。直至80年代,还是“反传统”的思潮支配人们走向现代化。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故,现代主义不再可能成为文学创新的路径,探索者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改弦易辙,这就是新写实主义试图对现实主义做些微调整重新出场的缘由。但真正深刻而内在的并且影响深远的改变却是由陕西作家做出来的。这就是90年代初,陈忠实带着《白鹿原》、贾平凹带着《废都》进京召开研讨会,俗称“陕军东征”。就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人而言,或许因为他们偏居秦地一隅,因为远离主流文坛而与时势慢了半拍;或许是因为秦地文化底蕴深厚,他们容易与传统文化接续上联系。“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在于它本质上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寻根作家群只能讲述知青故事,并不能讲述寻根的真正故事。但对于陈忠实和贾平凹慢了半拍的记忆而言,“寻根”依然记忆犹新,甚至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还恍如昨日。实际上,《白鹿原》和《废都》都带有“寻根文学”和“人性论”的流风余韵,只不过秦地文化的内涵这回是正面充实得足够分量。他们本来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写作,回到史传传统笔法中,古朴老旧的风格就让人惊异不已。
《白鹿原》在主流评论界被推为新时期以来首屈一指的长篇小说。虽然陈忠实谦逊地说,他写《白鹿原》受到了张炜《古船》的影响。其影响的根本就在于,张炜或许是新时期文学中以反思之名正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而陈忠实是90年代直接标举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第一人。陈忠实勾连出的不只是中国乡村的传统,同时还有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尽管我们一直用“现实主义”来表述它——在《白鹿原》中,与20世纪主流的现实主义相比较而言,更具生活本色的那种真实性,正是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在起作用。
小说描写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兴衰成败,荣辱更替,婚丧嫁娶,土地流转。象征着几千年宗族社会传统价值,然而又是杂乱更替的祠堂广场,与象征着现代暴力冲突的戏台交相对比,各自演绎着农业文明没落的传奇和剧烈变革的现代戏剧,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是20世纪大变局的到来。白、鹿两家后代都投入到了时代冲突中,不再是白、鹿两家的争雄,而是现代到来谁能辨识方向。事实上,茅盾和柳青都曾经回答了时代难题——当下中国的道路应做何选择?但是,陈忠实却是在思考,在“退一步”,但这并非倒退,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试图从“自然史”的大背景上来理解中国20世纪的剧变,农业文明及其文化传统在激进现代性的冲击下,似乎是衰败了。从小说开篇白嘉轩遭遇传宗接代的困境起笔,白嘉轩出门到白鹿原上,在早春的地里看到那棵象征着“白鹿”的小草,于是他用上好的水田换取了鹿子霖家的坡地。那块坡地是所谓的“风水宝地”,白家自然也获得了上天的惠顾,繁衍后代,人丁兴旺。但剧烈的千年变局,在白鹿原上硝烟迷漫。小说终了,鹿子霖已经疯傻,只会坐在地上挖掘野草。历经如此多的变故,白嘉轩以为自己早年用水田换了鹿子霖的旱地,夺了鹿家的风水,以至于鹿家遭受厄运,疯的疯,死的死。但小说的厉害就在这里,它引出中国传统“自然史”意义上的天道天意,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使得陈忠实在这里不得不留下历史到来的不确定性。在这部小说首尾呼应的结构中,隐藏着“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甚至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反讽暗喻——这何尝不是创造性转化呢?对于像历史大还是天意大这样的问题,陈忠实没有作答,或者说貌似作答,却是虚晃一枪,留给读者无限的思索。在20世纪的大变局中,陈忠实重新思考了传统文化,也是在这种思考和书写中,他为历史作传,为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正名,为当代中国文学书写大文明的传统竖起自己的纪念碑。
贾平凹的《废都》试图为90年代的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命名。固然作品对90年代初中国文化的反映并不周全和准确,但贾平凹却率先尝试恢复传统文学的命脉,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他想赓续《西厢记》《红楼梦》的文化传统。《废都》纵然有诸多问题,但他重建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自觉意识却无疑是可贵的。《废都》讲性情性灵,想追求古典美学的空灵飘逸一路的风格,却因为性描写招致激烈批评,贾平凹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一美学追求。他转向了另一面,回到泥土和大地的写作,随后写下《秦腔》《古炉》《山本》等一系列小说,但这三部作品可视为贾平凹的秦地三部曲。这些故事关乎乡土中国的文明在现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剧烈、血腥、暴力,这里的人们都是拿生命去换取现代的生存。这些作品在不断地提问:现代是文明的断裂还是更新呢?这些提问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让人无法作答。他越写越土,越写越狠,他不再讲述个人的故事,不再有空灵和性情,这里有大地和死亡,有衰败和哀恸。读一读贾平凹写这几部书的后记,他在不断地清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自己与乡土的血脉。写《废都》他去翻阅那些野史笔记;写《秦腔》他就到棣花镇看着年轻后生从城里回到村里抬棺材;写《带灯》他要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他伏在书桌上哭泣;他写《极花》要去感受中国的水墨画。他说 “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表达的正是他与传统的息息相通。除夕夜他回家乡到祖坟点灯,“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老生·后记》)。写《山本》,他在秦岭里走,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看着云从秦岭西往东流去,“突然省悟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山本·后记》)。贾平凹在这些书后记里表白道,他在语言上(美学上),他由明清而唐宋,由唐宋而秦汉。对他自己的再生而言,仿佛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历程。中国作家到了21世纪反倒更迫切地要建立起与文学传统的联系,他们在艰难的自我磨砺中试图完成回归传统的创新性发展。
相较于陈忠实和贾平凹,莫言的几部代表作更明确地聚焦于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引发的剧烈冲突,他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可被视为中国现代三部曲。莫言的作品书写20世纪中国民族经历的苦难历程,没有人像他那样彻底又富有激情,那样痛切又满怀英雄主义,那样放纵随心所欲又能截取独特角度。他没有回避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所经受的无穷无尽的动荡、蹂躏和艰辛,而是以其强劲的笔墨去写出历史的困境,写出中国人民战胜苦难的勇气、付出和惨痛。想想莫言写作《丰乳肥臀》这部作品,何等样的大手笔,写出一个母亲带着八个儿女穿行过20世纪中国惨烈的历史场景。张清华称《丰乳肥臀》是伟大的汉语小说,他说莫言笔下的母亲“所感受的世界既动荡又重复,她以不变的意志与方式承受和消化着一切灾难和变故,她所生发出的是悲壮和崇高的诗意”。莫言这是为她的母亲,为20世纪的中国母亲立传。确实有不少人对莫言书写苦难和暴力多有批评,但是,中国古老文明进入现代历经的惨烈却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作家是否有能力写出这样的历史,是对作家才胆识力的考验。莫言是能经受得住考验的作家之一,正如2012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莫言的颁奖辞里所说的:“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席卷?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的声音掩盖同侪。”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莫言的受奖答谢辞题目是《讲故事的人》,他却是低调地回到中国传统乡村。他说道:“《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幼时的经历,他跟随母亲到镇上的市集听说书人说书,那是他的文学启蒙。所谓“说书”,无非说史说事说人,虽然是民间故事传说,但所据是中国传统的史传演义。当然,莫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是最有抒情才能的作家,《红高粱家族》当年在艺术上的成功与它华美的抒情反讽笔调不无关系,那是在中国文学向现代主义进发的途中必要的放纵,因为这种放纵,中国的现代主义具有乡土中国的本性。他自己所钟爱的 《透明的红萝卜》,从小说题名就富有抒情意味,虽然是叙事类小说作品,但小说内里流宕着一股浓浓诗情。因为那个主人公黑孩——莫言多少有些自况的形象——他的沉默无语,如石头一般放置在小说中,冷硬坚固,这使得小说中吝啬地透出的些许爱意,那些描写和语言的放纵,象征乃至色彩的渲染,都具有了诗意抒情的特性。莫言说他从《檀香刑》开始后撤,按陈思和的观点,莫言是后撤至“民间的立场”,他想撇开“民间”的政治性元素。陈思和说,莫言的小说叙事里“不含有知识分子装腔作态的斯文风格,总是把叙述的原点置放在民间最本质的物质层面——生命形态上启动发轫”。回到民间,也是回到传统文化的根脉中。这种后撤绝不是让艺术单纯地变土、变得简单和保守,而是在传统的根脉中找到更加宽广、圆融、大气的文学之道。
洪治纲在分析《檀香刑》的艺术表现手法时指出:“国仇、家仇、情仇,以种种戏剧化的方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爱与恨、荣与辱、道义与亲情,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反复盘旋;尊严、良知、道义,构成了上至知识精英、下至黎民百姓的精神隐痛。他们挣扎,呼告,反击,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送上了刑场,在一种又一种超越想象力的刑罚过程中化为灰烬。”《檀香刑》采用了章回体,且有意以虎头、熊腰、猪肚、豹尾的结构特征来突出情节。小说叙述则用了山东地方戏茂腔,眉娘作为主导的叙述人,她的叙述最具有茂腔特点,并且以她为中心结构起所有的人物关系。在小说中,地位最为卑贱的民间女子,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最后是她手刃公爹——清朝最后一个刽子手,把小说推向高潮并走向结局。在莫言向传统和民间后撤时,他的小说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他是真正把中国民间说书人的口传艺术,把中国的史传传统与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结合一起,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李敬泽认为,“《檀香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大’这个词不会把《檀香刑》压垮”。他敏锐地指出:“《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同样是在全球背景下,我们要接续我们的根,建构起我们的传统,确立我们不可泯灭的文化特性。”这个“伟大性”就在于它如此强大有力地讲述了中国现代史,李敬泽阐释说:“‘历史’恰恰是必须言喻的,不被说出的一切就不是历史。正是通过‘说’,我们才会确定和皈依某种历史理性。”这就是说,莫言在为中国近现代史做传,作为历史真实性的证言,莫言承接中国伟大的“史传传统”——他说出了历史。莫言是少数把中国“史传传统”与“抒情传统”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作家,他的创作前期在叙事中总有浓重的抒情流宕其间;后期则是“史传传统”起主导作用,也会时有抒情修辞流露出来。
事实上,不只是莫言、陈忠实、贾平凹,以及其他创作出重要作品的一批作家,例如,铁凝、张炜、王安忆、阿来、刘震云、阎连科、格非、苏童、徐小斌、刘醒龙等曾经浸淫于外国文学的作家,在90年代以后都有向传统回归的愿望,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又努力把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与中国传统以及民间经验结合在一起,创作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精神和现代风格的作品。这就是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承继和生长,当代中国文学接续传统命脉而又开辟出面向未来的道路。
当今时代,一大批中国作家在走向世界,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正在被世界各国人民阅读,世界人民正在从文学中了解中国,接近中国,触摸中国,以情感和心灵来感受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创建文学的伟大传统,尤其需要中国当代文学来构筑这一伟大的传统。因此,在我们重视古代传统文学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去珍惜当代文学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需要重视这些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作家和评论家,需要文学评论去阐释这些重要作家和作品,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给予更为宽松的空间让文学的伟大传统生长,并且繁盛地生长下去。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是中国文化强盛的时代。
从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学就有一个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都被激进的反传统思潮所支配,处于进入现代剧烈变革中的中国,同时面临反帝反封建的重任,革命必须彻底,革命是解放和涅槃。直至80年代,还是“反传统”的思潮支配人们走向现代化。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故,现代主义不再可能成为文学创新的路径,探索者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改弦易辙,这就是新写实主义试图对现实主义做些微调整重新出场的缘由。但真正深刻而内在的并且影响深远的改变却是由陕西作家做出来的。这就是90年代初,陈忠实带着《白鹿原》、贾平凹带着《废都》进京召开研讨会,俗称“陕军东征”。就陈忠实和贾平凹两人而言,或许因为他们偏居秦地一隅,因为远离主流文坛而与时势慢了半拍;或许是因为秦地文化底蕴深厚,他们容易与传统文化接续上联系。“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在于它本质上是知青文学的变种,寻根作家群只能讲述知青故事,并不能讲述寻根的真正故事。但对于陈忠实和贾平凹慢了半拍的记忆而言,“寻根”依然记忆犹新,甚至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还恍如昨日。实际上,《白鹿原》和《废都》都带有“寻根文学”和“人性论”的流风余韵,只不过秦地文化的内涵这回是正面充实得足够分量。他们本来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写作,回到史传传统笔法中,古朴老旧的风格就让人惊异不已。
《白鹿原》在主流评论界被推为新时期以来首屈一指的长篇小说。虽然陈忠实谦逊地说,他写《白鹿原》受到了张炜《古船》的影响。其影响的根本就在于,张炜或许是新时期文学中以反思之名正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而陈忠实是90年代直接标举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第一人。陈忠实勾连出的不只是中国乡村的传统,同时还有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尽管我们一直用“现实主义”来表述它——在《白鹿原》中,与20世纪主流的现实主义相比较而言,更具生活本色的那种真实性,正是中国传统的“史传”笔法在起作用。
小说描写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兴衰成败,荣辱更替,婚丧嫁娶,土地流转。象征着几千年宗族社会传统价值,然而又是杂乱更替的祠堂广场,与象征着现代暴力冲突的戏台交相对比,各自演绎着农业文明没落的传奇和剧烈变革的现代戏剧,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是20世纪大变局的到来。白、鹿两家后代都投入到了时代冲突中,不再是白、鹿两家的争雄,而是现代到来谁能辨识方向。事实上,茅盾和柳青都曾经回答了时代难题——当下中国的道路应做何选择?但是,陈忠实却是在思考,在“退一步”,但这并非倒退,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试图从“自然史”的大背景上来理解中国20世纪的剧变,农业文明及其文化传统在激进现代性的冲击下,似乎是衰败了。从小说开篇白嘉轩遭遇传宗接代的困境起笔,白嘉轩出门到白鹿原上,在早春的地里看到那棵象征着“白鹿”的小草,于是他用上好的水田换取了鹿子霖家的坡地。那块坡地是所谓的“风水宝地”,白家自然也获得了上天的惠顾,繁衍后代,人丁兴旺。但剧烈的千年变局,在白鹿原上硝烟迷漫。小说终了,鹿子霖已经疯傻,只会坐在地上挖掘野草。历经如此多的变故,白嘉轩以为自己早年用水田换了鹿子霖的旱地,夺了鹿家的风水,以至于鹿家遭受厄运,疯的疯,死的死。但小说的厉害就在这里,它引出中国传统“自然史”意义上的天道天意,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使得陈忠实在这里不得不留下历史到来的不确定性。在这部小说首尾呼应的结构中,隐藏着“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甚至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反讽暗喻——这何尝不是创造性转化呢?对于像历史大还是天意大这样的问题,陈忠实没有作答,或者说貌似作答,却是虚晃一枪,留给读者无限的思索。在20世纪的大变局中,陈忠实重新思考了传统文化,也是在这种思考和书写中,他为历史作传,为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正名,为当代中国文学书写大文明的传统竖起自己的纪念碑。
贾平凹的《废都》试图为90年代的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命名。固然作品对90年代初中国文化的反映并不周全和准确,但贾平凹却率先尝试恢复传统文学的命脉,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他想赓续《西厢记》《红楼梦》的文化传统。《废都》纵然有诸多问题,但他重建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自觉意识却无疑是可贵的。《废都》讲性情性灵,想追求古典美学的空灵飘逸一路的风格,却因为性描写招致激烈批评,贾平凹也不得不放弃了这一美学追求。他转向了另一面,回到泥土和大地的写作,随后写下《秦腔》《古炉》《山本》等一系列小说,但这三部作品可视为贾平凹的秦地三部曲。这些故事关乎乡土中国的文明在现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剧烈、血腥、暴力,这里的人们都是拿生命去换取现代的生存。这些作品在不断地提问:现代是文明的断裂还是更新呢?这些提问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让人无法作答。他越写越土,越写越狠,他不再讲述个人的故事,不再有空灵和性情,这里有大地和死亡,有衰败和哀恸。读一读贾平凹写这几部书的后记,他在不断地清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自己与乡土的血脉。写《废都》他去翻阅那些野史笔记;写《秦腔》他就到棣花镇看着年轻后生从城里回到村里抬棺材;写《带灯》他要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他伏在书桌上哭泣;他写《极花》要去感受中国的水墨画。他说 “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表达的正是他与传统的息息相通。除夕夜他回家乡到祖坟点灯,“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老生·后记》)。写《山本》,他在秦岭里走,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看着云从秦岭西往东流去,“突然省悟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山本·后记》)。贾平凹在这些书后记里表白道,他在语言上(美学上),他由明清而唐宋,由唐宋而秦汉。对他自己的再生而言,仿佛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历程。中国作家到了21世纪反倒更迫切地要建立起与文学传统的联系,他们在艰难的自我磨砺中试图完成回归传统的创新性发展。
相较于陈忠实和贾平凹,莫言的几部代表作更明确地聚焦于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引发的剧烈冲突,他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可被视为中国现代三部曲。莫言的作品书写20世纪中国民族经历的苦难历程,没有人像他那样彻底又富有激情,那样痛切又满怀英雄主义,那样放纵随心所欲又能截取独特角度。他没有回避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所经受的无穷无尽的动荡、蹂躏和艰辛,而是以其强劲的笔墨去写出历史的困境,写出中国人民战胜苦难的勇气、付出和惨痛。想想莫言写作《丰乳肥臀》这部作品,何等样的大手笔,写出一个母亲带着八个儿女穿行过20世纪中国惨烈的历史场景。张清华称《丰乳肥臀》是伟大的汉语小说,他说莫言笔下的母亲“所感受的世界既动荡又重复,她以不变的意志与方式承受和消化着一切灾难和变故,她所生发出的是悲壮和崇高的诗意”。莫言这是为她的母亲,为20世纪的中国母亲立传。确实有不少人对莫言书写苦难和暴力多有批评,但是,中国古老文明进入现代历经的惨烈却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作家是否有能力写出这样的历史,是对作家才胆识力的考验。莫言是能经受得住考验的作家之一,正如2012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莫言的颁奖辞里所说的:“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席卷?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的声音掩盖同侪。”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莫言的受奖答谢辞题目是《讲故事的人》,他却是低调地回到中国传统乡村。他说道:“《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幼时的经历,他跟随母亲到镇上的市集听说书人说书,那是他的文学启蒙。所谓“说书”,无非说史说事说人,虽然是民间故事传说,但所据是中国传统的史传演义。当然,莫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是最有抒情才能的作家,《红高粱家族》当年在艺术上的成功与它华美的抒情反讽笔调不无关系,那是在中国文学向现代主义进发的途中必要的放纵,因为这种放纵,中国的现代主义具有乡土中国的本性。他自己所钟爱的 《透明的红萝卜》,从小说题名就富有抒情意味,虽然是叙事类小说作品,但小说内里流宕着一股浓浓诗情。因为那个主人公黑孩——莫言多少有些自况的形象——他的沉默无语,如石头一般放置在小说中,冷硬坚固,这使得小说中吝啬地透出的些许爱意,那些描写和语言的放纵,象征乃至色彩的渲染,都具有了诗意抒情的特性。莫言说他从《檀香刑》开始后撤,按陈思和的观点,莫言是后撤至“民间的立场”,他想撇开“民间”的政治性元素。陈思和说,莫言的小说叙事里“不含有知识分子装腔作态的斯文风格,总是把叙述的原点置放在民间最本质的物质层面——生命形态上启动发轫”。回到民间,也是回到传统文化的根脉中。这种后撤绝不是让艺术单纯地变土、变得简单和保守,而是在传统的根脉中找到更加宽广、圆融、大气的文学之道。
洪治纲在分析《檀香刑》的艺术表现手法时指出:“国仇、家仇、情仇,以种种戏剧化的方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爱与恨、荣与辱、道义与亲情,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反复盘旋;尊严、良知、道义,构成了上至知识精英、下至黎民百姓的精神隐痛。他们挣扎,呼告,反击,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被送上了刑场,在一种又一种超越想象力的刑罚过程中化为灰烬。”《檀香刑》采用了章回体,且有意以虎头、熊腰、猪肚、豹尾的结构特征来突出情节。小说叙述则用了山东地方戏茂腔,眉娘作为主导的叙述人,她的叙述最具有茂腔特点,并且以她为中心结构起所有的人物关系。在小说中,地位最为卑贱的民间女子,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最后是她手刃公爹——清朝最后一个刽子手,把小说推向高潮并走向结局。在莫言向传统和民间后撤时,他的小说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他是真正把中国民间说书人的口传艺术,把中国的史传传统与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结合一起,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李敬泽认为,“《檀香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伟大’这个词不会把《檀香刑》压垮”。他敏锐地指出:“《檀香刑》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向,同样是在全球背景下,我们要接续我们的根,建构起我们的传统,确立我们不可泯灭的文化特性。”这个“伟大性”就在于它如此强大有力地讲述了中国现代史,李敬泽阐释说:“‘历史’恰恰是必须言喻的,不被说出的一切就不是历史。正是通过‘说’,我们才会确定和皈依某种历史理性。”这就是说,莫言在为中国近现代史做传,作为历史真实性的证言,莫言承接中国伟大的“史传传统”——他说出了历史。莫言是少数把中国“史传传统”与“抒情传统”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作家,他的创作前期在叙事中总有浓重的抒情流宕其间;后期则是“史传传统”起主导作用,也会时有抒情修辞流露出来。
事实上,不只是莫言、陈忠实、贾平凹,以及其他创作出重要作品的一批作家,例如,铁凝、张炜、王安忆、阿来、刘震云、阎连科、格非、苏童、徐小斌、刘醒龙等曾经浸淫于外国文学的作家,在90年代以后都有向传统回归的愿望,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又努力把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与中国传统以及民间经验结合在一起,创作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精神和现代风格的作品。这就是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承继和生长,当代中国文学接续传统命脉而又开辟出面向未来的道路。
当今时代,一大批中国作家在走向世界,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正在被世界各国人民阅读,世界人民正在从文学中了解中国,接近中国,触摸中国,以情感和心灵来感受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创建文学的伟大传统,尤其需要中国当代文学来构筑这一伟大的传统。因此,在我们重视古代传统文学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去珍惜当代文学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需要重视这些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作家和评论家,需要文学评论去阐释这些重要作家和作品,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给予更为宽松的空间让文学的伟大传统生长,并且繁盛地生长下去。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中国发挥作用的时候,一定是中国文化强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