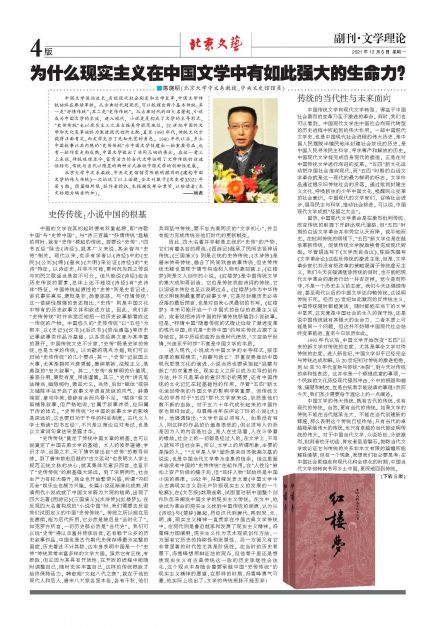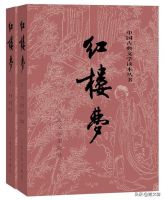当前位置:北京文艺2021年12月06日期 第04版:副刊·文学理论
为什么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晓明撰写的《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文论述了以上话题,全文刊载于《文史哲》2021年第5期。因篇幅所限,经作者授权,本报摘发部分章节,以飨读者(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史传传统:小说中国的根基
中国的文学在其初起时便有双重起源,即“诗歌中国”与“史传中国”。与“诗三百篇”“抒情传统”滥觞的同时,就有“史传”源起的传统。若要论“史传”,“四书五经”除去《诗经》,就其广义来说,其余皆与“史传”相关。现代以来,也多有学者以《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来论证《诗经》的“史诗”特征。以诗证史,并非不可能,更何况先民之传说与初民之歌谣当是密不可分。但只能说《诗经》包含历史传说的要素,总体上还不能说《诗经》有“史诗体”特征。中国传统起源性的“史传”则是史官记述,讲究事实真实,褒贬是非,扬善惩恶。与“抒情传统”这一修辞性颇强的表述相比,“史传”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历史叙事文体和叙述方法,因此,我们讲“史传传统”时并非宽泛地把一切历史叙事都看成这一传统的产物。中国悠久的“史传传统”以“五经”为根本,以《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记事叙事类作品为基础,以各类经典文章为其丰富的展开。中国传统文史不分家,“史传”既是史学的传统,也是文学的传统。以刘勰的观点为据,我们可以归纳“史传传统”的几个要点:其一,“史传”记叙国之大事,尤其是朝邦兴衰更替,赓续革新,法规正义,是典型的“宏大叙事”。其二,“史传”有鲜明的价值观,善恶分明,褒贬有度,用语谨慎。其三,“史传”讲究笔法精当,幽隐婉约,微言大义。当然,后世“赋体”或骈文铺陈手法开启了叙事文学语言放纵的风气,辞藻绚丽、章句华美,修辞有余而风骨不足。“赋体”骈文虽铺陈叙事,但严格地说,它属于叙事诗类,应归属于诗的体式。“史传传统”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也要归功于千年的科举制度。古代文人学士熟读“四书五经”,不只是以策论应对考试,也是以文章词句章法来显露才华。
“史传传统”奠定了传统中国文章的根基,也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文人的修养道德、学识才华、治国之术、天下情怀皆出自“史传”的教导训练。到了唐宋前赴后继的“古文运动”也表明文人学士规范正统文脉的决心;就其集体无意识而言,也宣示了“史传传统”的根基强大深远。到了宋明两代,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升,商业也开始繁荣兴盛,所谓“勾栏瓦舍”娱乐业也颇为兴隆。长篇小说逐渐演化成熟,明清两代小说成就了中国文学蔚为大观的格局,出现了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反观四大名著构成的“小说中国”时,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试图定义的中国“史传传统”。传统之所以能在后世赓续,能为后代所用,它必然是被后世“当时化了”。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必然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说“史传”得以丰富并传承后世,还有赖于众多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国也是古代朝代史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国度,历史著述不计其数,这本身表明中国是一个“史传”传统异常丰富多样的文学大国。虽然它有正统,有根脉,但正因为其具有开放性,在开放的进程中能随时调整自己,随时充实丰富自己,这样的传统根脉才始终保持活力。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在于他的同代人和后人,唐宋八大家各显本色,各有千秋,他们共同坚守传统,要不忘先秦两汉的“文学初心”,并且有能力完成传统在他们时代的更新蜕变。
因此,四大名著并非都是正统的“史传”的产物,它们有着各自的源流:《西游记》继承了民间志怪神话传统;《三国演义》则是正统的史传传统;《水浒传》是唐宋传奇传统,融合了民间戏曲故事传说,但史传传统无疑也显现于情节构造和人物形象刻画上;《红楼梦》则是文人创作的小说。《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集大成和再创造,它也是传统戏曲诗词的传统,它以词话本传世也足以说明这点。《红楼梦》作为中华传统文明晚期最重要的叙事文学,它是对封建历史必将没落的最后预言,也是对自我心灵最初的书写。《红楼梦》本来可能开启一个中国式的世俗的浪漫主义运动,或者说把诗词中国的抒情传统移植到小说叙事。但是,“抒情中国”随着传统的式微让位给了激进变革的现代中国,终究是“史传中国”的写实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历经的曲折当是时代使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啻是中国文学的本质。
进入现代,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导样式,按李泽厚的解释模式,“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小说当然也要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主导的创作方法,并不只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在起基础性的作用。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外国文学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传统文化的学养对于“五四”那代文学家来说,依然是他们剪不断的血脉。对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也同样如此。冯雪峰当年在评论丁玲的小说《水》时,他强调指出:“文学作品必须写人,如果没有写人,则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是很低的;但必须写人仍然是因为人的内容是社会,是人在生活着,人在斗争着的缘故。社会上的一切都是经过人的。在文学上,不写人就写不出社会来。所以,文学上的所谓形象,主要的是指的人。”“文学是人学”固然是来自苏俄高尔基的说法,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奉为圭臬的信条。但这里面未尝没有中国的“史传传统”在起作用。在“人性论”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后,但“写好人物”却始终是中国小说的典律。1952年,冯雪峰发表文章《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在《文艺报》数期连载,试图面对新中国整个创作队伍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中,他尝试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找到中国传统的渊源,认为从《诗经》与《楚辞》算起,历经汉代到唐代,再到宋、元、明、清,现实主义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在现代则是鲁迅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精神。冯雪峰力图阐明,现实主义作为艺术观或创作方法,一方面有它历史的持续性和发展性,另一方面又有它非常显著的时代性尤其是阶级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冯雪峰想用辩证法的观点,但他骨子里还是想使现实主义有古典传统这一脉的历史承继性合法化,这个观点本身隐含着要承继中国“史传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愿望,在那样的时期,冯雪峰勇气可嘉,他实际上说出了:文学的传统根脉不能丢弃!
传统的当代性与未来面向
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得益于中国社会剧烈的变革乃至于激进的革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伟大历史,是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奴役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寻求民主科学、寻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能完成自身现代的塑造,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深刻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向现代,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就是这一现代的最为鲜明的标志。文学作品通过揭示旧传统社会的没落,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呼唤新生的少年中国文化,唤醒民众变革的社会意识。中国现代的文学家们,召唤社会进步,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社会前进。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经国之大业”。
固然,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在激烈批判传统、改变传统的前提下开辟出现代道路,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并非凭空从天而降,或平地而生。在批判传统的纲领下,“五四”新文学也是在继承革新传统,促使传统文学脱胎换骨完成现代转型。尽管胡适写下《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撰写《文学革命论》这些反传统的激进主张,但是,文学革命家们并没有把改革的策略混淆于传统虚无主义。我们今天在强调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不能把现代文学革命的激进行动一并否定掉。觉今是而昨非,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今天还强调传统,甚至现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还仰赖传统,这说明传统不死。经历20世纪如此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国传统随时都能复活,随时都能在当下的文学中显灵,这究竟是中国社会的永久的保守性,还是说中国传统就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二者本质上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现代社会始终变革前进,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开始改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传统的态度,尤其是革命文学对待传统的态度。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学似乎已经完全与传统达成和解。从20世纪初对传统的激进拒绝,到50至70年代宣称与传统“决裂”,到今天对传统的亲和性表达,这并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项,一个民族的文化历经现代强烈冲击,个中的损毁和磨难、痛楚和蜕变,岂是白纸黑字能说清的事理?然而今天,我们至少需要给予理论上的一点阐述。
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既有古代的传统,也有现代的传统。当然,更有当代的传统。如果文学的传统不能在当代继承光大,不能在当代创建新的辉煌,那么表明这个传统已经终结;只有当代的卓越能承继伟大的传统,也只有卓越的当代能证明传统的伟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众说纷纭,分歧激烈,批判者咬牙切齿,肯定者坚若磐石。细数当代文学或论证它与传统的关系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解释清楚,但有一个现象,我想我们有必要思考:在中国社会更趋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却转向书写乡土中国,更深地回到传统。
(下转5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陈晓明撰写的《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文论述了以上话题,全文刊载于《文史哲》2021年第5期。因篇幅所限,经作者授权,本报摘发部分章节,以飨读者(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史传传统:小说中国的根基
中国的文学在其初起时便有双重起源,即“诗歌中国”与“史传中国”。与“诗三百篇”“抒情传统”滥觞的同时,就有“史传”源起的传统。若要论“史传”,“四书五经”除去《诗经》,就其广义来说,其余皆与“史传”相关。现代以来,也多有学者以《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来论证《诗经》的“史诗”特征。以诗证史,并非不可能,更何况先民之传说与初民之歌谣当是密不可分。但只能说《诗经》包含历史传说的要素,总体上还不能说《诗经》有“史诗体”特征。中国传统起源性的“史传”则是史官记述,讲究事实真实,褒贬是非,扬善惩恶。与“抒情传统”这一修辞性颇强的表述相比,“史传”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历史叙事文体和叙述方法,因此,我们讲“史传传统”时并非宽泛地把一切历史叙事都看成这一传统的产物。中国悠久的“史传传统”以“五经”为根本,以《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记事叙事类作品为基础,以各类经典文章为其丰富的展开。中国传统文史不分家,“史传”既是史学的传统,也是文学的传统。以刘勰的观点为据,我们可以归纳“史传传统”的几个要点:其一,“史传”记叙国之大事,尤其是朝邦兴衰更替,赓续革新,法规正义,是典型的“宏大叙事”。其二,“史传”有鲜明的价值观,善恶分明,褒贬有度,用语谨慎。其三,“史传”讲究笔法精当,幽隐婉约,微言大义。当然,后世“赋体”或骈文铺陈手法开启了叙事文学语言放纵的风气,辞藻绚丽、章句华美,修辞有余而风骨不足。“赋体”骈文虽铺陈叙事,但严格地说,它属于叙事诗类,应归属于诗的体式。“史传传统”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也要归功于千年的科举制度。古代文人学士熟读“四书五经”,不只是以策论应对考试,也是以文章词句章法来显露才华。
“史传传统”奠定了传统中国文章的根基,也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文人的修养道德、学识才华、治国之术、天下情怀皆出自“史传”的教导训练。到了唐宋前赴后继的“古文运动”也表明文人学士规范正统文脉的决心;就其集体无意识而言,也宣示了“史传传统”的根基强大深远。到了宋明两代,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升,商业也开始繁荣兴盛,所谓“勾栏瓦舍”娱乐业也颇为兴隆。长篇小说逐渐演化成熟,明清两代小说成就了中国文学蔚为大观的格局,出现了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反观四大名著构成的“小说中国”时,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试图定义的中国“史传传统”。传统之所以能在后世赓续,能为后代所用,它必然是被后世“当时化了”。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必然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说“史传”得以丰富并传承后世,还有赖于众多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国也是古代朝代史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国度,历史著述不计其数,这本身表明中国是一个“史传”传统异常丰富多样的文学大国。虽然它有正统,有根脉,但正因为其具有开放性,在开放的进程中能随时调整自己,随时充实丰富自己,这样的传统根脉才始终保持活力。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在于他的同代人和后人,唐宋八大家各显本色,各有千秋,他们共同坚守传统,要不忘先秦两汉的“文学初心”,并且有能力完成传统在他们时代的更新蜕变。
因此,四大名著并非都是正统的“史传”的产物,它们有着各自的源流:《西游记》继承了民间志怪神话传统;《三国演义》则是正统的史传传统;《水浒传》是唐宋传奇传统,融合了民间戏曲故事传说,但史传传统无疑也显现于情节构造和人物形象刻画上;《红楼梦》则是文人创作的小说。《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集大成和再创造,它也是传统戏曲诗词的传统,它以词话本传世也足以说明这点。《红楼梦》作为中华传统文明晚期最重要的叙事文学,它是对封建历史必将没落的最后预言,也是对自我心灵最初的书写。《红楼梦》本来可能开启一个中国式的世俗的浪漫主义运动,或者说把诗词中国的抒情传统移植到小说叙事。但是,“抒情中国”随着传统的式微让位给了激进变革的现代中国,终究是“史传中国”的写实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历经的曲折当是时代使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啻是中国文学的本质。
进入现代,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导样式,按李泽厚的解释模式,“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推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小说当然也要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主导的创作方法,并不只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在起基础性的作用。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外国文学的影响非常重要,但传统文化的学养对于“五四”那代文学家来说,依然是他们剪不断的血脉。对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也同样如此。冯雪峰当年在评论丁玲的小说《水》时,他强调指出:“文学作品必须写人,如果没有写人,则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是很低的;但必须写人仍然是因为人的内容是社会,是人在生活着,人在斗争着的缘故。社会上的一切都是经过人的。在文学上,不写人就写不出社会来。所以,文学上的所谓形象,主要的是指的人。”“文学是人学”固然是来自苏俄高尔基的说法,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奉为圭臬的信条。但这里面未尝没有中国的“史传传统”在起作用。在“人性论”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后,但“写好人物”却始终是中国小说的典律。1952年,冯雪峰发表文章《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在《文艺报》数期连载,试图面对新中国整个创作队伍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中,他尝试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找到中国传统的渊源,认为从《诗经》与《楚辞》算起,历经汉代到唐代,再到宋、元、明、清,现实主义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在现代则是鲁迅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精神。冯雪峰力图阐明,现实主义作为艺术观或创作方法,一方面有它历史的持续性和发展性,另一方面又有它非常显著的时代性尤其是阶级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冯雪峰想用辩证法的观点,但他骨子里还是想使现实主义有古典传统这一脉的历史承继性合法化,这个观点本身隐含着要承继中国“史传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愿望,在那样的时期,冯雪峰勇气可嘉,他实际上说出了:文学的传统根脉不能丢弃!
传统的当代性与未来面向
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得益于中国社会剧烈的变革乃至于激进的革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伟大历史,是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奴役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寻求民主科学、寻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能完成自身现代的塑造,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深刻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向现代,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就是这一现代的最为鲜明的标志。文学作品通过揭示旧传统社会的没落,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呼唤新生的少年中国文化,唤醒民众变革的社会意识。中国现代的文学家们,召唤社会进步,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社会前进。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经国之大业”。
固然,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在激烈批判传统、改变传统的前提下开辟出现代道路,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并非凭空从天而降,或平地而生。在批判传统的纲领下,“五四”新文学也是在继承革新传统,促使传统文学脱胎换骨完成现代转型。尽管胡适写下《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撰写《文学革命论》这些反传统的激进主张,但是,文学革命家们并没有把改革的策略混淆于传统虚无主义。我们今天在强调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不能把现代文学革命的激进行动一并否定掉。觉今是而昨非,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今天还强调传统,甚至现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还仰赖传统,这说明传统不死。经历20世纪如此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国传统随时都能复活,随时都能在当下的文学中显灵,这究竟是中国社会的永久的保守性,还是说中国传统就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二者本质上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现代社会始终变革前进,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开始改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传统的态度,尤其是革命文学对待传统的态度。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学似乎已经完全与传统达成和解。从20世纪初对传统的激进拒绝,到50至70年代宣称与传统“决裂”,到今天对传统的亲和性表达,这并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项,一个民族的文化历经现代强烈冲击,个中的损毁和磨难、痛楚和蜕变,岂是白纸黑字能说清的事理?然而今天,我们至少需要给予理论上的一点阐述。
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既有古代的传统,也有现代的传统。当然,更有当代的传统。如果文学的传统不能在当代继承光大,不能在当代创建新的辉煌,那么表明这个传统已经终结;只有当代的卓越能承继伟大的传统,也只有卓越的当代能证明传统的伟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众说纷纭,分歧激烈,批判者咬牙切齿,肯定者坚若磐石。细数当代文学或论证它与传统的关系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解释清楚,但有一个现象,我想我们有必要思考:在中国社会更趋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却转向书写乡土中国,更深地回到传统。
(下转5版)